自從去年年底華為CFO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之后,一向低調的華為便成為了世界新聞的中心焦點;而在美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打擊華為的舉措之后,華為更被國人目為抵抗美帝的英雄。
任正非不再是一個隱藏在幕后的隱形大佬。他頻繁地出現在電視、媒體和公眾視域之中。他真正地成為了企業明星:或許,這根本就不是他的初衷所愿,而僅僅是情不得已。
他的個人魅力顯然征服了公眾。就我自己而言,就是路轉粉的典型之一。中國的企業多有向權力尋租的內在驅動,即便在天下太平之時,也往往以民族主義,國貨當自強,愛國品牌等蠱惑世人。殊不知,真正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往往自我隱蔽,甚至偽裝成所在國品牌。企業以趨利為根本目標,錢銀歸入總部,政治偽裝越是本地化,越是有利于企業。我猜想華為在之前,大約也是如此。
因而,任正非完全可以在這樣的一個非常時期,大打愛國牌,杯葛美國政府,從而換取政府同情,國民情緒,以便獲得更大的利益。然而相反,他一再強調美國是一個法制國家,相信法律公正,贊許美國企業的專業與幫助,呼吁向美國的發展模式學習。
這自然是一種冷靜的企業思考,也是一種令人敬佩的格局情懷。在此家國碰撞,危機四伏的年代里,從個人到企業到家國,越是冷靜與制度化的應對,便越是有利整體問題趨緩。這樣的思維與行為,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需要巨大的智慧與勇氣,,委實令人膺服。
1.
然而,我隱隱感到一些不安。許多人認為,任正非5月21日第二次接受央視面對面專訪,這是任正非不屈服于美國封殺華為的底氣,更是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但我卻看見其中幾個不安的信息。
其一,任正非所展示的那張二戰中美國被打殘的飛機的圖片。這張照片表面上所傳達的的確是勇氣與堅韌。但是試問,哪個企業,哪個實體愿意置之死地而后生?也就是說,任正非無非在預測未來的情形將會一場慘烈的戰爭;

任正非對未來的預測如此慘烈
其二,他對董倩再三強調的再窮不能窮教育。你可以說這是任正非的執念,亦是他的胸懷。但基礎教育的事情,什么時候講都不晚,什么時候都應該講,什么場合下都可以講。然而,一個正在漩渦之中的企業領袖,在央視平臺、黃金時間講基礎教育,必定有弦外之音。
因而,我以為任正非最近的多次訪談之中,都只是微言大義。我甚至極端地認為,這是任正非的呼救信號,三個層面:
其一,向國民呼救。在幾乎所有的訪談中,任正非都一再強調以美為師的看法,并且呼吁不要煽動民族情緒。在這個非常的時期中,把華為作為民族工業的英雄,送到與美國對抗的前線,這其實是把華為放到火上烤。特朗普政府先殺中興,再打華為,所需要的恰恰是一個能夠成為中國象征的企業代表,華為越是被裝扮成英雄,越成為特朗普政府的口實。因此,不煽動民族情緒,不以華為為代表與美國對抗,方才是對華為最良善的支持;
其二,向政府呼救。基礎教育為何重要?因為它乃是民族競爭的終極武器。現代世界的競爭,是制度、科技、文化、管理、資本、人才、軍力的全面競爭。一個企業再大,再有力,再先進,也無從與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抗衡。華為富可敵國,而若成為美國”國可敵富“的典型,只怕同樣兇多吉少。與其說此時談基礎教育如何重要,不若是談國家競爭如何可能。基礎教育是國家競爭力之呈現,以基礎教育,談國家競爭戰略,這或者才是任正非的言外之意。
其三,向內部呼救。華為四面受敵,美國攜軍事合作與貿易互惠以令各國,西方國家遲早、多少都會屈服,華為的困難不會僅僅是美國的,并且可能會是更多西方盟國的。值此四面楚歌之際,唯有內部同心戮力,穩住那架即將被打穿的飛機,方才有希望涉險過關,徐圖再起。
任正非向國內世界是如此傳達的信息,向外部世界依然是傳達這樣的信息:華為非抗美英雄,企業不過是圖利工具,做好最壞的打算。
對于華為如此密集的公關行動,以及一直一貫的信息,我只是隱隱覺得哪里有些不對。5月初,我的朋友劉小彪的文章《華為公關得失的10個問題》,耙梳了華為對外公關中的歷程,并歷數其中的技術得失,自然是十分專業與負責的真知灼見,然而我始終以為未中肯綮,而仍然是技術分析。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
直到6月17日任正非的咖啡現場對話,與尼葛洛龐帝、喬治·吉爾德大談互聯網與未來時,我才恍然大悟過來:原來華為這半年來的公關行動,實在是戰略上失去了大焦點。因而技術上的成功,也未能扭轉格局上的失利,美國政府無動于衷,更加步步緊逼,而華為和任正非只能放棄幻想、悲情背水備戰。
2.
如何理解華為今日的困境?卻必須從美國政治說起。
許多人未能洞悉此次美國國內政情與國情變化的根本,簡單地說,就是特朗普上臺,美國民意右轉與地緣戰略重提。
從冷戰結束以來,期間歷經了共和民主兩黨的多位總統,從克林頓開始,到小布什,再到奧巴馬,期間與中國的齟齬并不少,雙方劍拔弩張的情形也有多回。說到意識形態,小布什班底的新保守主義,從哲學上才是最重視意識形態抗爭的。然而,40年來美國始終與中國保持良好合作態勢,并且曾經一度提到戰略合作伙伴的高度。是如何一夜變天的?特朗普真能一手遮天?
事實上,特朗普的上臺,本身就是美國國內民情變化的一個結果。美國此次國民集體右轉,其本質不過是反全球化運動的一個情緒反彈而已。
冷戰之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態勢,以及貿易邊界的打破,全球范圍內產業鏈分工格局的形成,的確提升了整個世界的經濟發展。可惜,一切都是不完美的。
從美國國內來說,新經濟所帶來的變化,使美國經濟的整體競爭力上升了,產業升級,技術升級,知識升級。但是,它是以傳統經濟的崩潰為代價的。所有人的都知道,低勞動技能型工作外包,傳統制造業和加工業外逃,這是美國的一個普遍現狀。底特律等傳統汽車工業城市奄奄一息,而硅谷則欣欣向榮。
換句話說,知識精英、金融精英與文化精英收割了所有的利益,反而把底層工業和底層階層推向了破產。這不是危言聳聽,早在2000年世代開始,包括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哥大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都曾經發出過警世恒言;英國出生的歷史學家托尼·朱特更從來憂心忡忡于福利社會的崩潰。
特朗普并不是因為中國問題上臺的,而是因為“美國夢斷”而上臺的。美國夢不是專為精英設計的,它是給下層一個打破階級秩序,沖頂人生的機遇。精英階層一夜暴富,下層群眾日益蕭條。這便是美國傳統工業與底層階級所看到的現實——全球化所帶來的現實。

特朗普抓住的,是底層階級的憤怒與恐懼。
并不是因為他們愛特朗普,他們只是要推翻精英階層的壟斷。哪怕是條狗說出了這個事實,承諾改變,他們都會選它。
更加糟糕的是:全球的全球化都在退潮。歐洲的難民問題,中東的恐怖主義,非洲與拉美的發展瓶頸。只有穩定和平的東亞在悶聲發大財。
地緣戰略的重提日程,并不是世界要重回冷戰熱戰的意識形態戰爭,不過是全球化經濟利益的重新分配。中國首當其沖。
好了,話說得有點復雜了,這一切與華為的公關有什么關系?
我以為,華為的公關行動不斷地加重美國國內既有的判斷,日益把自己更加嚴重地描繪成美國的敵人。
到目前為止,華為的公關重點概括有三:1,中國國內的主流媒體,包括央視以及數十家國內頂尖媒體,目的為爭取國內支持,團結內部力量;2,歐美主流媒體,包括BBC、時代周刊、紐約時報等,傳達華為聲音,打消或減弱美國政府的敵對情緒,爭取民意支持;3,美國精英群體,包括華為的美國合作方、尼葛洛龐帝以及美國大學,獲取美國民間力量支持,穩定合作方關系。
只可惜,這三個方向,全都是與美國當前國情為敵的公關。公關越成功,美國對華為的打擊就越名正言順,越有的放矢。
3.
還要澄清一個問題:無論華為做什么,都不可能與中國政治脫鉤。
特朗普發動對華為的征伐,看起來像是大炮打蚊子,以一國之力打擊一個企業,看似用力過猛,又似小人行徑。
(這是我最為討厭特朗普政府行為模式的一個典型案例。美國政府向來是價值觀優先的,且不論對錯。公義、公平與政治倫理,一直都是美國政府的行動指針,也是向國會乃至民眾征詢同意的假定前提。武力力量,只不過是支持這種道德行動的必要手段。然而,特朗普政府破壞一切程序,一切皆出于目的需求。這不僅違背了美國的政治程序,也在無限透支美國倫理價值。這已經為未來美國的全球地位埋下了深厚禍根。)
到目前為止,特朗普政府對華為的打擊,都是有目的的政治行動。按照美國的司法體系,假如美國方面已經掌握了華為“從事間諜行為”的實錘證據,早就已經入呈法院。FBI、CIA、NSA,哪個部門是吃素的?這么大的案子,所有部門都會搶著來辦,何須政府在那里聒噪。在以往中美都曾有過如此案例,政府從來未曾如此高調介入。
于是,當特朗普政府將華為列為政治打擊對象時,中國政府不可能置身事外的。有些天真的論調以為華為自證清白即可,殊不知特朗普政府不過是以華為敲山震虎,試探底線,若是中國政府不介入,美國政府便可以對中國企業肆意妄為。對于雙方政府而言,華為已經淪為一個談判籌碼,其背后便是千萬中國企業在美國的生死存亡。
那么,既然是一個綁架式的政治行為,那么華為的公關不能高調反擊,如今反倒像是推波助瀾?
就國內而言,華為儼然已經成為抗美英雄,前文已然詳述。國內的媒體越是甚囂塵上,美國民意便會越是認為,華為的確是中國力量代表。任正非在國內媒體中多次提到,華為不怕美國的封殺,華為愿意付出犧牲美國市場的代價,華為是打不死的鳥。當這些信息傳達的美國的時候,無非就是向美國政府與公眾強調,華為愿意與美國政府對抗,甚至與整個美國對抗。華為事實就成了對抗美國的先鋒戰士。那么,特朗普政府打擊華為的政治行為,還有錯嗎?難道不是更加名正言順了嗎?
同樣,在這半年來任正非接受了大量歐美主流媒體的采訪,從新聞雜志,到主流報紙,到公共電視臺,也的確不斷傳達華為只是一家民間企業,華為技術先進,華為與人為善的信息。
只是不知道華為的公關以及他所雇傭的那些公關公司知不知道一件事情:美國到底是誰在看這些媒體?
簡單答案:精英群體。
精英傳媒根本無法將聲音傳達到底層。精英傳媒如今已然無法影響政府決策。再說得殘酷一些吧,我看到任正非所接受采訪的傳媒,基本上都是左派傳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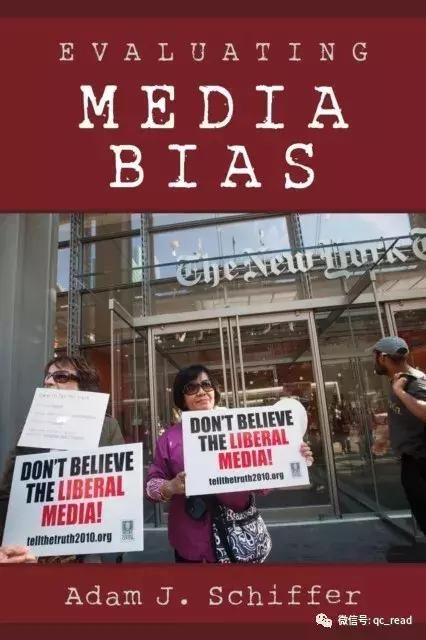
底層與右派,從對精英媒體的不滿,上升為攻擊。
近些年來,隨著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挺進,美國的傳播生態已經發生幾乎是顛覆性的根本轉變。在傳統媒體時代,精英媒體掌握話語權,對于公共事務有很強的發言權,甚至能夠左右白宮政策。
互聯網使信息多元化瞬間實現,而即時性和互動性,慢慢消解和侵蝕了傳統媒體的壟斷性。但是,美國的媒體精英拒絕改變,依然以慣性的、居高臨下的、社會看門狗的形象,維持了日益下墜的尊嚴。
但年輕一代和普通公眾卻再也不買賬了,甚至嗤之以鼻。他們要自己的話語權,他們要自己的信息渠道。
普通的民眾看八卦,玩社交網站,看YouTube,Facebook,地方報紙,地方電視臺,有線電視。精英傳媒的影響力,都在發達、全球化的、互聯網化的東西兩岸和紐約洛杉磯這些發達城市。
而在全球化中受損的那批人,甚至越來越把其中一部分的責任,歸咎于左派精英媒體的毫無保留的全球化立場。
他們開始反對左派精英媒體。
右派精英有它們自己的一套體系,既不融入于左派所控制的媒體產業,也與大眾興致無關。他們形成了自己的一套幾乎封閉的文化體系:福克斯電視臺、《國家利益》雜志、傳統基金會。
特朗普和他的政府成員們只看這些。但是,他們非常積極地,甚至瘋狂地擁抱社交媒體。
所以,當任正非以為在面向歐美公眾喊話的時候,哎呀,他只被那一小撮左派精英所聽見。
可是這批左派精英啊,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到奧巴馬到特朗普,他們的思維和語言范式從來沒有改變過:全球化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這些人,說與不說,他們都不會幫著特朗普反華為。
你看,華為這么龐大的公關行動和公關投入,對于反對華為的人,只是不斷在加深他們的偏見和定見;對于那些支持華為的人,卻幾乎是無效的重復信息。
4.
美國的精英左派,到現在都沒有明白他們為什么輸給了特朗普;或者起碼有一部分人,知道為什么輸了,卻也不愿意為此而改變。
他們的的確確是輸在了民意基礎之上。在美國歷史上,從來的選舉就是在效率與公平之上走平衡木。發展過快就選保守派,共和黨;發展過慢就選自由派,民主黨。屢試不爽。
反全球化根本是什么?公平問題。精英階層收割過大,底層失速,快速貧困。但是這次略有些不同的地方在于,連右派精英都是全球化的得利者,所以他們連右派精英都不選,找了個局外人。
特朗普沒有什么哲學理念,他本質上就是一個反智的、反全球分工的、反技術進步的傳統產業保守派,或者說是實用性保守主義者。在他的政綱和施政行動中看不到任何的保守主義結構建樹,而全面是實用主義的見招拆招。
但是他無疑是一個非常聰明和精明的實用性政治,他的選舉就是越過了所有既有的政治建制,而直接訴諸底層。他甚至撇開了保守派傳媒,而全面地利用了社交媒體,滲透、控制、扭曲甚或改變選民的心智,從而一舉獲得了優勢的底層支持。
贏,就是他的政治綱領。
硅谷的互聯網精英,東岸的知識精英,好萊塢的文化精英,還在喋喋不休地抨擊特朗普胡作非為,反移民、反貿易、反互聯網。其中有些人其實已經看到了特朗普利用民族主義和底層憤怒的社會情緒,但是他們太鐘情于全球化,太鐘情于社會進步,他們不肯回到底層。
而特朗普的每個動作,都在向底層階級表忠心。
底層,就是特朗普的票倉。傳統制造業、傳統石油產業、傳統商業、傳統工業,傳統農業,傳統勞工。你以為美國真的有多發達?廣袤的中西部、德克薩斯的農業、五大湖區,全都是傳統行業。

底特律的蕭條,已然被美國人看成是美國全球化受損的一個象征。
特朗普的三板斧:以振興工業反對工作外流;以遏制中國反對金融外流;以反對貿易協議,整合地緣戰略力量。
死守著全球化的左派精英,束手無策。
再回頭來講華為公關了。
華為想要通過精英媒體和精英群體向美國傳達的信息,根本到達不了美國的底層階級。
長久以來,美國的底層階級基本上市依靠公共信息平臺和媒體來接受資訊。并且由于美國長期的宗教傳統和保守傳統,他們幾乎很少接受外來的信息。
公共平臺信息已被政府接管,以往的精英媒體不再起作用。甚而有之,對于精英傳媒的疑慮已經逐漸正在轉變成反感。左派傳媒《紐約時報》、《時代周刊》、CBS正在全面退出底層市場;而右派的福克斯電視臺、地方小報正在高歌猛進。
于是,華為通過精英媒體的喊話,反而正在加強美國公眾對于華為的偏見,而不是消解。
任正非善意地表揚合作的美國商業公司,并不能引發好感。這些以全球化獲益的公司,目前在美國國內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任何一個國家的企業,都與政治風向相捆綁。如果繼續保持與華為的緊密關系,他們自己在未來都難免不受到政府審查甚至制裁。
公眾的民族主義情緒與反精英情緒,是他們非常害怕的一個方向。和中國企業一樣,他們也是在廣大的消費者那里討生活的。政治風向一變,他們也得跟著愛國起來。
東岸的左派精英正在失去土地。在這場美國國內如火如荼的反全球化運動中,他們實在是有點out of context(毫無頭緒)。以往一呼百應的全球化論調,正在反過來變成扼殺他們的武器;西岸的互聯網精英和好萊塢精英暫時太平無事,美國仍然需要他們的力量來作為驅動力。但是在這一輪重振底層力量的努力里,他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也只能閉嘴。
右派精英首鼠兩端。在麥凱恩那一代守正持中的右派精英去世之后,現在的右派精英在特朗普的節節勝利中驚慌失措,無所適從。他們既沒有能力來抗衡特朗普,又不愿意失去自己在全球化中所獲得的超額利潤。
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順著潮流走。他們已經開始拋棄原有的政治建制,向特朗普投降,以求明哲保身。
整個精英階層幫不上華為一個手指頭。左派精英雖有同情,卻只能空談誤國:對上無法與特朗普政府對話,對下無法對底層階級產生影響力。右派精英避之唯恐不及。
5.
國內的力量不能用,精英媒體沒有用,精英群體不要用。那么華為公關能做什么?
這就是我說的,華為公關的戰略失焦:華為應該爭取的,是美國的民情所在,也就是特朗普的票倉,也就是美國的底層階級。
我很奇怪的是:像華為這種公司,都是打人民戰爭起家的,怎么到了這么個時候,反而看不清楚了呢?
特朗普的票倉是臨時性的,實用性的,搖擺性的,既不是無懈可擊,也不是固若金湯。
對于底層階級來說,他們對于特朗普是將信將疑的。這個來自于”口銜金湯匙“階級的人,自身劣跡斑斑,家庭身家巨億,他會誠心誠意地改變底層狀況?他們不關心他們的地緣戰略,不關心他的遏制戰略,但特朗普的演講卻在這個時刻打中了他們惴惴不安的靈魂:就業、公平、生活質量、移民與福利。
當特朗普把所有的一切,都包裝得與公平、與美國夢相關的時候,他就贏了。
要贏得與特朗普的戰爭,便需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公關策略上直接訴諸美國底層。
要打破特朗普通過打擊華為來保障美國底層利益的這個包裝,把華為一直一貫的信息,傳達到底層階級的眼皮子底下、耳朵里、心里去:華為在美國的商業,將會節省美國的成本,將會降低每個美國人的通信成本,將會為美國創造龐大的就業機會,將會有助于提升美國人的生活質量。
向特朗普的政治行動妥協或退讓不是華為的有效反擊,因為會帶來整個西方國家的連鎖反應。反過來將特朗普一軍,讓華為成為美國底層人的朋友,協助者,就業的創造者,而不是美國的敵人,美國的破壞者。
從技術上說,撇開所有的精英媒體,到民間去,上山下鄉,深入互聯網,挺進Facebook和YouTube,在Instagram里灌水,進入地方媒體,創造美國人民喜聞樂見的社交媒體帖子,制造美國人民奔走相告的視頻,進入美國人民的社區,揭露特朗普的謊言和惡毒……
哈哈,是的,就是在美國底層那里,打一場人民戰爭。
特朗普的第二屆任期選舉即將開始,他根本就不怕精英,他怕的是他的票倉的搖動。美國左派從來沒有搞清楚這件事情,華為應該要搞清楚。
這樣的公關行動,肯定要比邀請一些美國精英媒體、精英知識階層,要來的更加緩慢、痛楚與低效,但這是釜底抽薪,這也是唯一的辦法。
但這個戰略是有邊界的,它并不是要倒特。特朗普的一攬子美國改造計劃,是針對當下底層階級的需求而打造的,在美國國內無人能夠挑戰;在國際層面上,也無人能夠撼動:因為這是美國國內政治現實的根本。
華為的目的,只需要改變底層公眾對華為的看法,讓特朗普的票倉對他產生壓力。凡是特朗普票倉要他做的,他都會做。
這種小范圍、單一訴求的改變,是可實現的。特朗普根本不會冒任何票倉被動搖的風險。他的”敵人數據庫“里多的是儲備,換一個就是了。
這的確是一個怪現狀:中國的企業,從來就沒有搞清楚這個選舉制國家的政治結構。他們在國內習慣于發動底層,但到了美國,卻反而只抓住精英。
至少,這對華為,是一個改變被動局面的時機。
然而,這的確是全球化一個極端痛楚的時刻,幾乎沒有人能夠幸免于難。一場本應該只是修正全球化弊端的變革,變成了一場重啟全球爭斗的新對峙。在這個dark moment,我只有一點微薄的期望,就是在這個焦土之上,我們這些俗世的塵埃,能夠得以遠離兵燹,得小解脫。






